有一种说法:社会学的主流是非理论的。我大概就属于这个主流。自从在美国学了社会学,就对理论产生了反感,后来就常常感到自己成了"理论上的残疾人"。当然,我不应当拿北美社会学的实证主流为自己辩护,不喜欢理论本是我内心的倾向。
我也不想用自己长大的环境为自己辩护--我总觉得,我生活的前三十年(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人犯了一种"理论过多症",各种所谓"理论"充斥于我们的生活,连二十岁的大学生都言必称"主义"。记得我在匹兹堡大学的导师、著名历史社会学家许倬云先生有一次感慨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大陆来的学生说起话来怎么总爱用些大名词。的确,就像一个人因为吃某种东西太多吃伤了一样,我对理论就有这种感觉。由此你可以知道,当我看到弗雷泽所说的"我确信,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弗雷泽,孙珉编,第9页)这句话时,我为什么会对他怀有共鸣甚至是有点感激的心情。
对妇女个人生活史的访问和记录这一研究方法受到女权主义的高度重视,认为使用这种方法能够打破已有的边界,创造出新的公众话语。由于在过去的公众话语中,男性为主的色彩很重,因此女人的生活史在公众话语中的出现比起一般的个案生活史更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它有助于打破以男性话语为主的公众话语,使两性的话语在公众话语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女权主义在研究的访谈方法中偏爱半结构化的访谈方式。这是一种定性的(qualitative)调查技术。它既不同于采用参与观察方法的民族学方法(ethnography);也不同于传统的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缺少互动的大型结构性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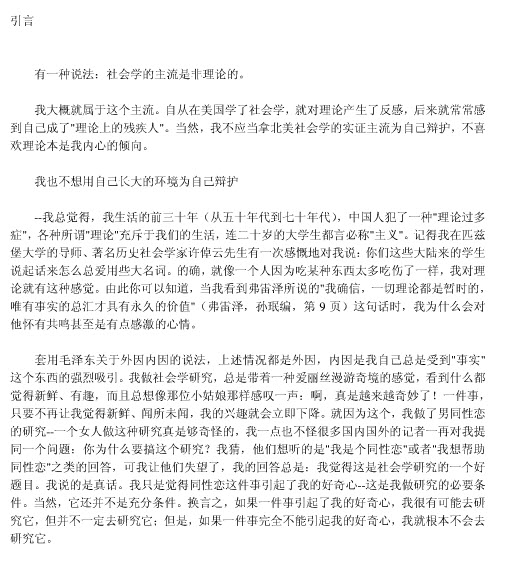

 大小: 3.0M
大小: 3.0M

 JS css jquery html5中文手册打包
JS css jquery html5中文手册打包  jQuery EasyUIv1.7.0官方API中文版
jQuery EasyUIv1.7.0官方API中文版  2015现金流量表模板excel模板免费下载
2015现金流量表模板excel模板免费下载  2015年最新损益表表格(利润表表格 excel版 )word版
2015年最新损益表表格(利润表表格 excel版 )word版  seek68客户端文献下载器12.0.1 官方最新版
seek68客户端文献下载器12.0.1 官方最新版  jsp高级编程教程PDF高清版
jsp高级编程教程PDF高清版  寨卡病毒ppt课件
寨卡病毒ppt课件  《赠言大全》(经典名言)上、下PDF电子书
《赠言大全》(经典名言)上、下PDF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