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娟
“白天”已经回家,“黑夜”还在继续。
陈明远留下一封信,然后爬上一座楼的楼顶。被拦下后的他被舅舅带回了湖南老家。陈明远上火车的时候,他的舍友刘效林没有去送他。
在全中国,每年有2亿多农民离开家乡,踏上外出打工之路。陈明远和刘效林,是这个群体里的一对合租者。他们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陈明远上白班,刘效林上晚班,彼此时间正好错开。
他们和他们所处的群体一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断裂。
失效的节俭
一张床的价值被最大化,成为“二十四小时热炕”
尽管是室友,刘效林与陈明远并不熟悉。他们在一次郊游活动中认识了,两个人都想从宿舍中搬出去住,于是,开始合租。他们租的房在深圳一个叫塘前小区的居民楼六楼。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一室一厅,麻雀般五脏俱全。进门的厅里,除了一只黑色的行李箱外,没有任何东西。小房间里放着一张床,占据了小房间里三分之二的面积。
整个房间只有一张床。陈明远和刘效林把时间有效地错开了。陈明远对应的是“白天”,他上白班,晚上回来睡觉。刘效林是“黑夜”,白天回来睡觉。这一张床的价值被最大化,成为“二十四小时热炕”。
“为了省钱,房租是200元一个月,加上水电费,分摊下来一个人只有一百出头。”刘效林说。这个合租房里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洗衣机,水电费少得惊人。
他们和亿万农民工一样,为了解决家庭的经济问题,从一处流动到另外一处打工。他们所在的城市深圳,堪称“打工者”最多的一座城市,现有的外来务工人数达到了700万之多。他们所在的企业富士康,也算得上中国代工企业的典范,光深圳园区就有40余万员工。
一个没有疑问的原因是,刘效林和陈明远选择合租是由于贫困或节俭。
1990年,中国农民工的人数不过才2135万。20年后,这个数字达到2.29亿。在中国的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已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这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更多向政府和企业集中。
按照刘效林的说法,富士康的待遇在珠三角算不错了,但即使如此,算上一个月大约100个小时的加班,也只有1500至2000元。
“其实,他们的薪水要比他们的父辈更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工人可能只有五六百元。但那时候的五六百元要值钱得多,那时的工人可以迅速地积累一笔小财富,回家盖个房,开个小店,过上不同的生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
这使他们面临的局面比父辈们面临的要残酷得多:节俭已经失效。
梦想与模仿
尽管贫穷,但他们渴望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从他们的打扮上可以看出来
他们怀着梦想在异乡打工。
尽管贫穷,但他们渴望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从他们的打扮上可以看出来。
陈明远爱漂亮,穿得很时髦,因为怕发炎,左边耳洞里塞着一个茶叶梗。刘效林比他大四岁,看上去像另外一种人,穿得最多的是厂服,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有一种少年老成的味道。
他们都愿意下一些本钱把自己打扮得更为时尚一些。在富士康,也随处可见模仿“非主流”的年轻人。这并不意味着一些调查的说法是对的——新一代农民工比他们的前辈要娇气、自私,实际上,他们在私下里过得节俭得多。
他们只是在模仿一种城市的生活。模仿的对象变了,呈现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在富士康,陈明远和刘效林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陈明远的梦想是当一个中医,像李时珍一样上山采药治病救人。这在现实中显得很遥远。
刘效林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年轻人,与其说梦想,不如说是计划更恰当些,他只想做点小生意,在充沛的体力减弱之前,可以进入另一种生活状态。
富士康今年第一个极端事件主角马向前生前的木床板上有几行字迹:“铭记自己种下的誓言:我将于2008年达成月薪创下5000元,如果达到目标,我将在街头磕三个响头。为了过富人生活的誓言,将改变我的一生。”
无法断定这是不是马向前的笔迹,但这行字代表了青年打工群体中很多人的梦想。“我希望能赚足够多的钱,然后回去考驾照,开个货车。”来自重庆的一个普工许超说。令他懊恼的是,现在每个月的工资最终都会所剩无几。
女性普工的梦想更实际些,19岁的甘肃女工巩小娟,从15岁开始出来打工,现在每个月可以往家里寄1000元,她对未来的想法就是回到家乡开个小店,然后嫁人生子过稳定的生活。
党国英说,对于青年农民工群体,模仿城市生活可能在更多意义上是个象征,意味着摆脱目前的境遇。
彩票的作用
在富士康龙华园区的北门,每个月发工资的几天,彩票站点的生意总是好得出奇
他们愿意模仿城市的生活。但城市的生活并不因为他们的模仿而离他们更近。
“城市欢迎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但并不欢迎他们的定居,企业有订单的时候拼命招收农民工,但也不喜欢农民工成为固定工。”党国英说。
深圳市一家权威机构所做的关于新生代民工的一份调查显示,在最大的生活问题排序上,排名第一的是“收入低”,“生活枯燥”排在第二位,第三位是“难以在城市立足”。
尽管政府在作出不懈的努力,希望能改善农民工的境遇,但城市的根本逻辑、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根本逻辑都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农民工的立场。富士康为农民工准备了“三金”,准备了清洁的食物和符合规定的加班费,那是为了能够不违法以及在企业的旺季能够有足够多的劳动力。
比如说,户籍。富士康系列极端事件之后,深圳开始调整现行的户籍政策,6月23日,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提出深圳的外来劳务工们将有可能通过积分制度获得深圳户口,要让劳动者体面劳动、快乐生活。
要成为一个“城里人”,房子几乎已经成为必备条件之一,心怀梦想的农民工们也必须得拥有一个永远都实现不了的收入。
在这点上,刘效林只是有些沮丧,他不想回去,但也没有试着在城市里落户。他从来没有关注过富士康大水坑观澜厂区周边的房价,在他想象中,这个价格很高,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或许比他想的更高。刘效林打工所在的宝安区,已经成为深圳又一高档住宅片区,其中心区楼盘的起价均在2万元/平方米以上,就算偏远些的地方,房价也要达到7000元/平方米以上。
按照这个价格,刘效林打两辈子工也难以在深圳立足。
在深圳的普工们中间流传着一条新闻:2009年8月,富士康一名21岁广西小伙子购买福利彩票中1327万元大奖。
这让大家都满怀天上掉馅饼的“期待”。在富士康龙华园区的北门,每个月发工资的几天,彩票站点的生意总是好得出奇。
青春·谎言·爆发
感情成为他们这一代工人情绪爆发的一个导火索。“为了女朋友才来到富士康,来了之后又分手了。”
超越自己的境遇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但他们还有青春。正是这些无法排遣、无人关注的青春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北门,东清湖村,狭小的区域里聚集了数十家黑网吧。这些网吧由农民房改造而成,压上两块钱就可以上两个小时的网,记者看到,大部分的年轻男性都在玩游戏,相反,女性都是以看电视和娱乐新闻为主,他们的共同点是都穿着工厂里的厂服。
这些网吧的电脑中还存放着大量成人电影。就算是白天,偶尔也会有人打开来看一看。
富士康龙华园区的北门,网吧旁边很多房间被改造了,一些穿着暴露、打扮时髦的年轻女郎不时走来走去,偶尔会有一些男工上前搭话,然后上楼。
青春的躁动被“武藤兰”、“苍井空”们不断消磨。
在富士康大水坑观澜园区附近的一家妇科医院,记者了解到,每天有大概二三十例流产手术,在周边,同等规模的妇科医院,大概有十多家。
这是女性普工遇到最难以启齿的问题,一个做完手术不久后的女工,电话里和男友谈到了分手,情绪突然失控,在歇斯底里发作后,把手机从七楼扔了下来。
她不知道的是,男友之所以要分手,是因为对另外一个差不多年龄的女工“有了感觉”。
感情成为他们这一代工人情绪爆发的一个导火索。陈明远也一样。“为了女朋友才来到富士康,来了之后又分手了。”
谎言成为年轻男女分手前的征兆,比如陈明远的女朋友,同样用谎言“稳住”了陈明远。这让19岁的陈明远感觉到很大的“挫败感”,他有点不愿意说,“这是想离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2010年5月31日,在床上躺了两天后,陈明远留下一封信。信里说,儿子活着真的好苦啊,还多次提及到父母和他之间感情的隔阂。
这是所有问题堆积在一起后的总爆发。
断裂
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个普遍困境是:既不想回到农村,也没办法呆在城里
陈明远被舅舅带回家没两天,就在想什么时候再出来打工。他觉得自己和没有出来的朋友不一样了,“毕竟见过世面了。”从外表看,他要比家乡的朋友穿得入时,但陈明远认为自己改变的不仅仅是外表,回家他已经觉得有些不适应了。
“一直做一个很奇怪的梦,梦到有一个男人从楼顶张开手臂飞了下去。”
如果说这寓意着逃离,通过摆脱环境来解决现有的问题的话,他现在又迫不及待想回到原来的环境中去。用毛寿龙的话来说,陈明远开始有了“身份认同障碍”。
相比陈明远,刘效林要顺利得多。刘效林现实、谨慎、理性,才23岁就已是富士康IDPBG(数字产品事业群)的一个线长。这个事业群生产了苹果公司的大部分代工产品。
得到线长的职务和他的经历有一定关系。在之前一次内部招聘上,有一个专门针对英文的考试,刘效林在中专学的英文帮了他大忙。他说,他告诉面试官,之前换过很多份工作,时间最长的是在东莞一个手表厂里做测试。
这个细节很大程度上帮了他的忙。在其后不到一年里,他很快被提拔为“线长”,这比一般人要快很多。“这一年时间我都没出过任何错。”他想了想,这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但即使是刘效林,也知道在这里并非长久之计。“基本上‘线长’已经到头了。”他很了解,凭现在的学历,要再往上爬,几乎是“难于上青天”。
工厂也试图提供“很大的空间”给他们,像富士康的IE学院,很多技工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来完成进修。但刘效林说:“换一个地方,也不知道通用不通用。”
工厂按照自己的逻辑给工人提供便利,甚至人生规划,但这很大程度上仅仅对工厂有利,对工人来说,这种规划,只是“被规划”了而已。在深圳的那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中,工作上最大问题排序中,“没发展机会、工作没成就感、工作机械能力没提高”被依次排在前三位。
中国的城镇化在迅速展开——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为17.9%,2009年,这个数字飙升到46.59%。国土资源部一份“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报告显示,1998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9.45亿亩,2008年仅为18.257亿亩(人均仅1.37亩),呈现出持续减少的势头,平均每年净减少耕地1300多万亩。根据测算,目前我国失地农民总数在5000万人左右,中国打工群体到了刘效林、陈明远这一代,不仅积累一笔能够改变生活的财富是个幻想,而且其中很多也回不去了,因为能够耕种的农田在不断缩小,也因为务农的收入无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
“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个普遍困境是:既不想回到农村,也没办法呆在城里。”毛寿龙分析说。这是农民工们必须要面对的最大断裂。他们打工,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外。
在陈明远回家之后,刘效林开始上白班,“黑夜”开始转换成“白天”,他没有觉得生活有什么不一样,除了每个月多负担一百多元的房租。
“年纪轻,就是要拿命搏钱啊,但肯定会走,没有人会在这里呆很久。”刘效林说,你看,这里打工的都是18~25岁。
但任何工厂都是一样的。打工,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人生的一种过法。
“黑夜”和“白天”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迟早都会离开这个地方。
至于明天,谁知道呢?

 U澶у笀v4.7.37.56 鏈€鏂扮増
U澶у笀v4.7.37.56 鏈€鏂扮増 HD Tune Prov5.75 姹夊寲缁胯壊鐗瑰埆鐗�
HD Tune Prov5.75 姹夊寲缁胯壊鐗瑰埆鐗� DiskGenius 涓撲笟鐗圴5.2.1.941 瀹樻柟鐗�
DiskGenius 涓撲笟鐗圴5.2.1.941 瀹樻柟鐗� 360杞欢绠″v7.5.0.1460 瀹樻柟鏈€鏂扮増
360杞欢绠″v7.5.0.1460 瀹樻柟鏈€鏂扮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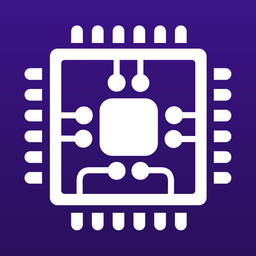 Cpu-Z涓枃鐗坴1.98.0 缁胯壊涓枃鐗�
Cpu-Z涓枃鐗坴1.98.0 缁胯壊涓枃鐗� 鑵捐鐢佃剳绠″V15.2 瀹樻柟姝e紡鐗�
鑵捐鐢佃剳绠″V15.2 瀹樻柟姝e紡鐗� office2016婵€娲诲伐鍏穔msv19.5.2 瀹樻柟鏈€鏂扮増
office2016婵€娲诲伐鍏穔msv19.5.2 瀹樻柟鏈€鏂扮増 杩呴浄11鏈€鏂扮増v11.3.6.1870 瀹樻柟鐗�
杩呴浄11鏈€鏂扮増v11.3.6.1870 瀹樻柟鐗� 360鍏嶈垂wifi5.3.0.5000 瀹樻柟鏈€鏂扮増
360鍏嶈垂wifi5.3.0.5000 瀹樻柟鏈€鏂扮増 360瀹夊叏娴忚鍣�2022v13.1.5188.0 瀹樻柟姝e紡鐗�
360瀹夊叏娴忚鍣�2022v13.1.5188.0 瀹樻柟姝e紡鐗� 閰锋垜闊充箰鐩�2022v9.1.6.2 瀹樻柟姝e紡鐗�
閰锋垜闊充箰鐩�2022v9.1.6.2 瀹樻柟姝e紡鐗� 鏆撮褰遍煶2021V5.81.0202.1111瀹樻柟姝e紡鐗�
鏆撮褰遍煶2021V5.81.0202.1111瀹樻柟姝e紡鐗� 蹇挱5.0姘镐笉鍗囩骇鐗�5.0.80 楠ㄥご鐗�
蹇挱5.0姘镐笉鍗囩骇鐗�5.0.80 楠ㄥご鐗� 浼橀叿2022瀹㈡埛绔疺8.0.9.11050 瀹樻柟鏈€鏂扮増
浼橀叿2022瀹㈡埛绔疺8.0.9.11050 瀹樻柟鏈€鏂扮増 鐖卞鑹鸿棰慥13.1.5瀹樻柟瀹夊崜鐗�
鐖卞鑹鸿棰慥13.1.5瀹樻柟瀹夊崜鐗� photoshop cs6 涓枃鐗�13.1.2.3 鍏嶈垂涓枃鐗�
photoshop cs6 涓枃鐗�13.1.2.3 鍏嶈垂涓枃鐗�![Autodesk 3ds Max 2012瀹樻柟绠€浣撲腑鏂囩増[32&64]](https://p.e5n.com/up/2018-9/2018921055101508.png) Autodesk 3ds Max 2012瀹樻柟绠€浣撲腑鏂囩増[32&64]
Autodesk 3ds Max 2012瀹樻柟绠€浣撲腑鏂囩増[32&64] CAD2007鍏嶈垂涓枃鐗�
CAD2007鍏嶈垂涓枃鐗� vc杩愯搴�2019鏈€鏂扮増v2019.3.2(32&64浣�)
vc杩愯搴�2019鏈€鏂扮増v2019.3.2(32&64浣�) .NET Framework 4.8瀹樻柟鐗�4.8.3646
.NET Framework 4.8瀹樻柟鐗�4.8.3646 QQ2022v9.5.6.28129 瀹樻柟鏈€鏂扮増
QQ2022v9.5.6.28129 瀹樻柟鏈€鏂扮増 寰俊鐢佃剳鐗�2022v3.5.0.44 瀹樻柟姝e紡鐗�
寰俊鐢佃剳鐗�2022v3.5.0.44 瀹樻柟姝e紡鐗� 鍗冪墰鍗栧宸ヤ綔骞冲彴v9.02.02N 瀹樻柟鐗�
鍗冪墰鍗栧宸ヤ綔骞冲彴v9.02.02N 瀹樻柟鐗� QT璇煶V4.6.80.18262瀹樻柟鏈€鏂扮増
QT璇煶V4.6.80.18262瀹樻柟鏈€鏂扮増 椋炰俊2018V6.2.0700 瀹樻柟姝e紡鐗�
椋炰俊2018V6.2.0700 瀹樻柟姝e紡鐗� 渚犵洍椋炶溅缃伓閮藉競
渚犵洍椋炶溅缃伓閮藉競 楠戦┈涓庣爫鏉€缁翠含寰佹湇
楠戦┈涓庣爫鏉€缁翠含寰佹湇 铏愭潃鍘熷舰2
铏愭潃鍘熷舰2 浠ユ拻鐨勭粨鍚�
浠ユ拻鐨勭粨鍚� 鏉€鎵�5璧﹀厤
鏉€鎵�5璧﹀厤 H1Z1涓枃鐗�
H1Z1涓枃鐗� 瀛ゅ矝鎯婇瓊3
瀛ゅ矝鎯婇瓊3 涓夎娲茬壒绉嶉儴闃�6鎴橀槦涔嬪垉
涓夎娲茬壒绉嶉儴闃�6鎴橀槦涔嬪垉 浣垮懡鍙敜8:鐜颁唬鎴樹簤3
浣垮懡鍙敜8:鐜颁唬鎴樹簤3 鍚堥噾瑁呭5:骞荤棝
鍚堥噾瑁呭5:骞荤棝 娆ф床鍗¤溅妯℃嫙2
娆ф床鍗¤溅妯℃嫙2 鏃嬭浆杞儙
鏃嬭浆杞儙 鏋佸搧椋炶溅18
鏋佸搧椋炶溅18 绁炲姏绉戣帋
绁炲姏绉戣帋 F1 2015
F1 2015 鎴戠殑涓栫晫1.8.2
鎴戠殑涓栫晫1.8.2 娉版媺鐟炰簹
娉版媺鐟炰簹 楗ヨ崚:娴烽毦
楗ヨ崚:娴烽毦 鏄熺晫杈瑰
鏄熺晫杈瑰 鏈€鍚庣敓杩樿€匬C鐗�
鏈€鍚庣敓杩樿€匬C鐗� 鏂囨槑5:缇庝附鏂颁笘鐣�
鏂囨槑5:缇庝附鏂颁笘鐣� 涓夊浗蹇�12濞佸姏鍔犲己鐗�
涓夊浗蹇�12濞佸姏鍔犲己鐗� 淇¢暱涔嬮噹鏈�14濞佸姏鍔犲己鐗�
淇¢暱涔嬮噹鏈�14濞佸姏鍔犲己鐗� 闃挎彁鎷�:鍏ㄩ潰鎴樹簤
闃挎彁鎷�:鍏ㄩ潰鎴樹簤 甯濆浗鏃朵唬2寰佹湇鑰�
甯濆浗鏃朵唬2寰佹湇鑰� 鏀粯瀹濋挶鍖�(Alipay)V10.2.53.7000 瀹夊崜鐗�
鏀粯瀹濋挶鍖�(Alipay)V10.2.53.7000 瀹夊崜鐗� 鐧惧害鍦板浘瀵艰埅2022V15.12.10 瀹夊崜鎵嬫満鐗�
鐧惧害鍦板浘瀵艰埅2022V15.12.10 瀹夊崜鎵嬫満鐗� 鎵嬫満娣樺疂瀹㈡埛绔痸10.8.40瀹樻柟鏈€鏂扮増
鎵嬫満娣樺疂瀹㈡埛绔痸10.8.40瀹樻柟鏈€鏂扮増 鐣呴€旂綉鎵嬫満瀹㈡埛绔痸5.6.9 瀹樻柟鏈€鏂扮増
鐣呴€旂綉鎵嬫満瀹㈡埛绔痸5.6.9 瀹樻柟鏈€鏂扮増 鍗冭亰鐭ヨ瘑鏈嶅姟appv4.5.1瀹樻柟鐗�
鍗冭亰鐭ヨ瘑鏈嶅姟appv4.5.1瀹樻柟鐗� p2psearcher瀹夊崜鐗�7.3 鎵嬫満鐗�
p2psearcher瀹夊崜鐗�7.3 鎵嬫満鐗� 閰风嫍闊充箰2022瀹樻柟鐗圴11.0.8 瀹樻柟瀹夊崜鐗�
閰风嫍闊充箰2022瀹樻柟鐗圴11.0.8 瀹樻柟瀹夊崜鐗� 鐖卞鑹烘墜鏈虹増v13.1.0
鐖卞鑹烘墜鏈虹増v13.1.0 鐧惧害褰遍煶7.13.0 瀹樻柟鏈€鏂扮増
鐧惧害褰遍煶7.13.0 瀹樻柟鏈€鏂扮増 褰遍煶鍏堥攱v6.9.0 瀹夊崜鎵嬫満鐗�
褰遍煶鍏堥攱v6.9.0 瀹夊崜鎵嬫満鐗� 鑵捐鍔ㄦ极V9.11.5 瀹夊崜鐗�
鑵捐鍔ㄦ极V9.11.5 瀹夊崜鐗� 涔︽棗灏忚鍏嶈垂鐗堟湰v11.5.5.153 瀹樻柟鏈€鏂扮増
涔︽棗灏忚鍏嶈垂鐗堟湰v11.5.5.153 瀹樻柟鏈€鏂扮増 QQ闃呰鍣╝ppV7.7.1.910 瀹樻柟鏈€鏂扮増
QQ闃呰鍣╝ppV7.7.1.910 瀹樻柟鏈€鏂扮増 鎳掍汉鐣呭惉鍚功appv7.1.5 瀹樻柟瀹夊崜鐗�
鎳掍汉鐣呭惉鍚功appv7.1.5 瀹樻柟瀹夊崜鐗� 璧风偣璇讳功app鏂扮増鏈�20227.9.186 瀹夊崜鐗�
璧风偣璇讳功app鏂扮増鏈�20227.9.186 瀹夊崜鐗� 骞冲畨璇佸埜瀹塭鐞嗚储V9.1.0.1 瀹樻柟瀹夊崜鐗�
骞冲畨璇佸埜瀹塭鐞嗚储V9.1.0.1 瀹樻柟瀹夊崜鐗� 娴烽€氳瘉鍒告墜鏈虹増(e娴烽€氳储)8.71 瀹樻柟瀹夊崜鐗�
娴烽€氳瘉鍒告墜鏈虹増(e娴烽€氳储)8.71 瀹樻柟瀹夊崜鐗� 涓滄捣璇佸埜涓滄捣鐞嗚储4.0.5 瀹夊崜鐗�
涓滄捣璇佸埜涓滄捣鐞嗚储4.0.5 瀹夊崜鐗� 涓摱璇佸埜绉诲姩鐞嗚储杞欢6.02.010 瀹樻柟瀹夊崜鐗�
涓摱璇佸埜绉诲姩鐞嗚储杞欢6.02.010 瀹樻柟瀹夊崜鐗� 鍗庨緳璇佸埜灏忛噾鎵嬫満鐞嗚储杞欢3.2.4 瀹夊崜鐗�
鍗庨緳璇佸埜灏忛噾鎵嬫満鐞嗚储杞欢3.2.4 瀹夊崜鐗� 绂忓缓鍐滄潙淇$敤绀炬墜鏈洪摱琛屽鎴风2.3.4 瀹夊崜鐗�
绂忓缓鍐滄潙淇$敤绀炬墜鏈洪摱琛屽鎴风2.3.4 瀹夊崜鐗� 鏄撳埗浣滆棰戝壀杈慳pp4.1.16瀹夊崜鐗�
鏄撳埗浣滆棰戝壀杈慳pp4.1.16瀹夊崜鐗� 涓浗宸ュ晢閾惰鎵嬫満閾惰appV7.0.1.2.5 瀹夊崜鐗�
涓浗宸ュ晢閾惰鎵嬫満閾惰appV7.0.1.2.5 瀹夊崜鐗� 涓浗閾惰鎵嬫満閾惰瀹㈡埛绔�7.2.5 瀹樻柟瀹夊崜鐗�
涓浗閾惰鎵嬫満閾惰瀹㈡埛绔�7.2.5 瀹樻柟瀹夊崜鐗� 鑵捐鐚庨奔杈句汉鎵嬫満鐗圴2.3.0.0 瀹樻柟瀹夊崜鐗�
鑵捐鐚庨奔杈句汉鎵嬫満鐗圴2.3.0.0 瀹樻柟瀹夊崜鐗� 鍔茶垶鍥㈠畼鏂规鐗堟墜娓竩1.2.1瀹樻柟鐗�
鍔茶垶鍥㈠畼鏂规鐗堟墜娓竩1.2.1瀹樻柟鐗� 楗ラタ椴ㄩ奔杩涘寲鏃犻檺閽荤煶鐗坴7.8.0.0瀹夊崜鐗�
楗ラタ椴ㄩ奔杩涘寲鏃犻檺閽荤煶鐗坴7.8.0.0瀹夊崜鐗� 妞嶇墿澶ф垬鍍靛案鍏ㄦ槑鏄�1.0.91 瀹夊崜鐗�
妞嶇墿澶ф垬鍍靛案鍏ㄦ槑鏄�1.0.91 瀹夊崜鐗� 鍦颁笅鍩庣獊鍑昏€卋t鐗�1.6.3 瀹樻柟鐗�
鍦颁笅鍩庣獊鍑昏€卋t鐗�1.6.3 瀹樻柟鐗� 瑁呯敳鑱旂洘1.325.157 瀹夊崜鐗�
瑁呯敳鑱旂洘1.325.157 瀹夊崜鐗� 鍦f枟澹槦鐭㈤泦缁搗4.2.1 瀹夊崜鐗�
鍦f枟澹槦鐭㈤泦缁搗4.2.1 瀹夊崜鐗� 閬ぉ3D鎵嬫父1.0.9瀹夊崜鐗�
閬ぉ3D鎵嬫父1.0.9瀹夊崜鐗� 瀹夊崜妞嶇墿澶ф垬鍍靛案2榛戞殫鏃朵唬淇敼鐗圴1.9.5 鏈€鏂扮増
瀹夊崜妞嶇墿澶ф垬鍍靛案2榛戞殫鏃朵唬淇敼鐗圴1.9.5 鏈€鏂扮増 涔辨枟瑗挎父2v1.0.150瀹夊崜鐗�
涔辨枟瑗挎父2v1.0.150瀹夊崜鐗� 淇濆崼钀濆崪3鏃犻檺閽荤煶鏈€鏂扮増v2.0.0.1 瀹夊崜鐗�
淇濆崼钀濆崪3鏃犻檺閽荤煶鏈€鏂扮増v2.0.0.1 瀹夊崜鐗� 鍙h鑻遍泟鍗曟満鐗�1.2.0 瀹夊崜鐗�
鍙h鑻遍泟鍗曟満鐗�1.2.0 瀹夊崜鐗� 灏忓皬鍐涘洟瀹夊崜鐗�2.7.4 鏃犻檺閲戝竵淇敼鐗�
灏忓皬鍐涘洟瀹夊崜鐗�2.7.4 鏃犻檺閲戝竵淇敼鐗� 鐧诲北璧涜溅2鎵嬫父1.47.1 瀹夊崜鐗�
鐧诲北璧涜溅2鎵嬫父1.47.1 瀹夊崜鐗� 涓€璧锋潵椋炶溅瀹夊崜鐗坴2.9.14 鏈€鏂扮増
涓€璧锋潵椋炶溅瀹夊崜鐗坴2.9.14 鏈€鏂扮増 璺戣窇鍗′竵杞︽墜鏈虹増瀹樻柟鏈€鏂扮増v1.16.2 瀹夊崜鐗�
璺戣窇鍗′竵杞︽墜鏈虹増瀹樻柟鏈€鏂扮増v1.16.2 瀹夊崜鐗� 鐙傞噹椋欒溅8鏋侀€熷噷浜戜慨鏀圭増(鍏嶆暟鎹寘)v4.6.0j 閲戝竵鏃犻檺鐗�
鐙傞噹椋欒溅8鏋侀€熷噷浜戜慨鏀圭増(鍏嶆暟鎹寘)v4.6.0j 閲戝竵鏃犻檺鐗� 鐧句箰鍗冪偖鎹曢奔2021鏈€鏂扮増5.78 瀹夊崜鐗�
鐧句箰鍗冪偖鎹曢奔2021鏈€鏂扮増5.78 瀹夊崜鐗� 姊﹀够鍓戣垶鑰呭彉鎬佺増1.0.1.2瀹夊崜鐗�
姊﹀够鍓戣垶鑰呭彉鎬佺増1.0.1.2瀹夊崜鐗� 浠欏浼犺ro澶嶅叴瀹夊崜鐗�1.20.3鏈€鏂扮増
浠欏浼犺ro澶嶅叴瀹夊崜鐗�1.20.3鏈€鏂扮増 姊﹀够璇涗粰鎵嬫父鐗�1.3.6 瀹樻柟瀹夊崜鐗�
姊﹀够璇涗粰鎵嬫父鐗�1.3.6 瀹樻柟瀹夊崜鐗� 鐜嬭€呰崳鑰€V3.72.1.1 瀹夊崜鏈€鏂板畼鏂圭増
鐜嬭€呰崳鑰€V3.72.1.1 瀹夊崜鏈€鏂板畼鏂圭増 璋佸灏忚溅寮烘墜鏈虹増v1.0.49 瀹夊崜鐗�
璋佸灏忚溅寮烘墜鏈虹増v1.0.49 瀹夊崜鐗� mac纾佺洏鍒嗗尯宸ュ叿(Paragon Camptune X)V10.8.12瀹樻柟鏈€鏂扮増
mac纾佺洏鍒嗗尯宸ュ叿(Paragon Camptune X)V10.8.12瀹樻柟鏈€鏂扮増 鑻规灉鎿嶄綔绯荤粺MACOSX 10.9.4 Mavericks瀹屽叏鍏嶈垂鐗�
鑻规灉鎿嶄綔绯荤粺MACOSX 10.9.4 Mavericks瀹屽叏鍏嶈垂鐗� Rar瑙e帇鍒╁櫒mac鐗坴1.4 瀹樻柟鍏嶈垂鐗�
Rar瑙e帇鍒╁櫒mac鐗坴1.4 瀹樻柟鍏嶈垂鐗� Mac瀹夊崜妯℃嫙鍣�(ARC Welder)v1.0 瀹樻柟鏈€鏂扮増
Mac瀹夊崜妯℃嫙鍣�(ARC Welder)v1.0 瀹樻柟鏈€鏂扮増 Charles for MacV3.9.3瀹樻柟鐗�
Charles for MacV3.9.3瀹樻柟鐗� 鎼滅嫍娴忚鍣╩ac鐗坴5.2 瀹樻柟姝e紡鐗�
鎼滅嫍娴忚鍣╩ac鐗坴5.2 瀹樻柟姝e紡鐗� 閿愭嵎瀹㈡埛绔痬ac鐗圴1.33瀹樻柟鏈€鏂扮増
閿愭嵎瀹㈡埛绔痬ac鐗圴1.33瀹樻柟鏈€鏂扮増 蹇墮mac鐗坴1.3.2 瀹樻柟姝e紡鐗�
蹇墮mac鐗坴1.3.2 瀹樻柟姝e紡鐗� 鏋佺偣浜旂瑪Mac鐗�7.13姝e紡鐗�
鏋佺偣浜旂瑪Mac鐗�7.13姝e紡鐗� Apple Logic Pro xV10.3.2
Apple Logic Pro xV10.3.2 Adobe Premiere Pro CC 2017 mac鐗坴11.0.0 涓枃鐗�
Adobe Premiere Pro CC 2017 mac鐗坴11.0.0 涓枃鐗� 鍗冨崈闈欏惉Mac鐗圴9.1.1 瀹樻柟鏈€鏂扮増
鍗冨崈闈欏惉Mac鐗圴9.1.1 瀹樻柟鏈€鏂扮増 Mac缃戠粶鐩存挱杞欢(MacTV)v0.121 瀹樻柟鏈€鏂扮増
Mac缃戠粶鐩存挱杞欢(MacTV)v0.121 瀹樻柟鏈€鏂扮増 Adobe Fireworks CS6 Mac鐗圕S6瀹樻柟绠€浣撲腑鏂囩増
Adobe Fireworks CS6 Mac鐗圕S6瀹樻柟绠€浣撲腑鏂囩増 AutoCAD2015 mac涓枃鐗堟湰v1.0 瀹樻柟姝e紡鐗�
AutoCAD2015 mac涓枃鐗堟湰v1.0 瀹樻柟姝e紡鐗� Adobe Photoshop cs6 mac鐗坴13.0.3 瀹樻柟涓枃鐗�
Adobe Photoshop cs6 mac鐗坴13.0.3 瀹樻柟涓枃鐗� Mac鐭㈤噺缁樺浘杞欢(Sketch mac)v3.3.2 涓枃鐗�
Mac鐭㈤噺缁樺浘杞欢(Sketch mac)v3.3.2 涓枃鐗� Adobe After Effects cs6 mac鐗坴1.0涓枃鐗�
Adobe After Effects cs6 mac鐗坴1.0涓枃鐗� Adobe InDesign cs6 mac1.0 瀹樻柟涓枃鐗�
Adobe InDesign cs6 mac1.0 瀹樻柟涓枃鐗�![Mac鐗堝揩鎾�1.1.26 瀹樻柟姝e紡鐗圼dmg]](https://p.e5n.com/up/2014-8/201484111558.jpg) Mac鐗堝揩鎾�1.1.26 瀹樻柟姝e紡鐗圼dmg]
Mac鐗堝揩鎾�1.1.26 瀹樻柟姝e紡鐗圼dmg] Mac璇诲啓NTFS(Paragon NTFS for Mac)12.1.62 瀹樻柟姝e紡鐗�
Mac璇诲啓NTFS(Paragon NTFS for Mac)12.1.62 瀹樻柟姝e紡鐗� 杩呴浄10 for macv3.4.1.4368 瀹樻柟鏈€鏂扮増
杩呴浄10 for macv3.4.1.4368 瀹樻柟鏈€鏂扮増 Mac涓嬫渶寮哄ぇ鐨勭郴缁熸竻鐞嗗伐鍏�(CleanMyMac for mac)v3.1.1 姝e紡鐗�
Mac涓嬫渶寮哄ぇ鐨勭郴缁熸竻鐞嗗伐鍏�(CleanMyMac for mac)v3.1.1 姝e紡鐗� 鑻规灉BootCamp5.1.5640 瀹樻柟鏈€鏂扮増
鑻规灉BootCamp5.1.5640 瀹樻柟鏈€鏂扮増 寰俊ipad鐗�2020v7.0.12 瀹樻柟鐗�
寰俊ipad鐗�2020v7.0.12 瀹樻柟鐗� iphone鎵嬫満qq2021v8.5.0 瀹樻柟鐗�
iphone鎵嬫満qq2021v8.5.0 瀹樻柟鐗� 鏄撲俊iOS鐗坴7.3.13 iPhone鐗�
鏄撲俊iOS鐗坴7.3.13 iPhone鐗� 闄岄檶 iphoneV8.32.4 瀹樻柟姝e紡鐗�
闄岄檶 iphoneV8.32.4 瀹樻柟姝e紡鐗� 鍗冪墰 iphone鐗�9.2.5 瀹樻柟鐗�
鍗冪墰 iphone鐗�9.2.5 瀹樻柟鐗� 99涓ラ€夋渶鏂扮増V1.3.6
99涓ラ€夋渶鏂扮増V1.3.6 蹇墮iPhone鐗�5.7.3 瀹樻柟鐗�
蹇墮iPhone鐗�5.7.3 瀹樻柟鐗� 娣樺疂 for iPhonev9.5.15 瀹樻柟鏈€鏂扮増
娣樺疂 for iPhonev9.5.15 瀹樻柟鏈€鏂扮増 澧ㄨ抗澶╂皵 for iphoneV7.5.3瀹樻柟鏈€鏂扮増IPA
澧ㄨ抗澶╂皵 for iphoneV7.5.3瀹樻柟鏈€鏂扮増IPA 璋锋瓕鍦板浘iphone(Google Maps)4.54 涓枃鐗�
璋锋瓕鍦板浘iphone(Google Maps)4.54 涓枃鐗�![蹇挱鑻规灉鐗圴3.3.35 瀹樻柟鐗圼ipa]](https://p.e5n.com/up/2011-12/20111215155620.gif) 蹇挱鑻规灉鐗圴3.3.35 瀹樻柟鐗圼ipa]
蹇挱鑻规灉鐗圴3.3.35 瀹樻柟鐗圼ipa] 鍚夊悏褰遍煶鎾斁鍣╥os鐗�1.0.1017 鑻规灉ipad鐗�
鍚夊悏褰遍煶鎾斁鍣╥os鐗�1.0.1017 鑻规灉ipad鐗� 褰遍煶鍏堥攱鎾斁鍣╥os鐗�2.8.0 瀹樻柟鐗�
褰遍煶鍏堥攱鎾斁鍣╥os鐗�2.8.0 瀹樻柟鐗� 鏂楅奔鐩存挱瀹㈡埛绔痠os鐗�7.0.1 瀹樻柟鏈€鏂扮増
鏂楅奔鐩存挱瀹㈡埛绔痠os鐗�7.0.1 瀹樻柟鏈€鏂扮増 閰风嫍闊充箰 for iPhonev10.9.0 瀹樻柟鏈€鏂扮増
閰风嫍闊充箰 for iPhonev10.9.0 瀹樻柟鏈€鏂扮増 How old do I look ios鐗�1.02 瀹樻柟鐗�
How old do I look ios鐗�1.02 瀹樻柟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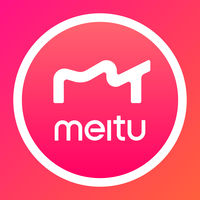 缇庡浘绉€绉€iPhone鐗圴8.6.62 鏈€鏂版寮忕増
缇庡浘绉€绉€iPhone鐗圴8.6.62 鏈€鏂版寮忕増 姘村嵃闃熼暱鑻规灉鐗坴1.0.0
姘村嵃闃熼暱鑻规灉鐗坴1.0.0 澶╁ぉp鍥緄pad鐗�5.7.4 瀹樻柟鐗�
澶╁ぉp鍥緄pad鐗�5.7.4 瀹樻柟鐗� 蹇墜ios鐗圴9.6.30 瀹樻柟鐗�
蹇墜ios鐗圴9.6.30 瀹樻柟鐗� 鑳屽寘鍦板浘ios鐗�1.0 瀹樻柟鏈€鏂扮増
鑳屽寘鍦板浘ios鐗�1.0 瀹樻柟鏈€鏂扮増 鎵嬫満瀹夊叏鍔╂墜鑻规灉鐗坴1.0 瀹樻柟鏈€鏂扮増
鎵嬫満瀹夊叏鍔╂墜鑻规灉鐗坴1.0 瀹樻柟鏈€鏂扮増 UC娴忚鍣╒113.5.5.1555涓枃鐗�
UC娴忚鍣╒113.5.5.1555涓枃鐗� 360娴忚鍣℉D for iPadV4.1.3 姝e紡鐗�
360娴忚鍣℉D for iPadV4.1.3 姝e紡鐗� iPhone鎵嬫満QQ娴忚鍣╒8.9.1 瀹樻柟鐗�
iPhone鎵嬫満QQ娴忚鍣╒8.9.1 瀹樻柟鐗�
 喜欢
喜欢  顶
顶 难过
难过 囧
囧 围观
围观 无聊
无聊





